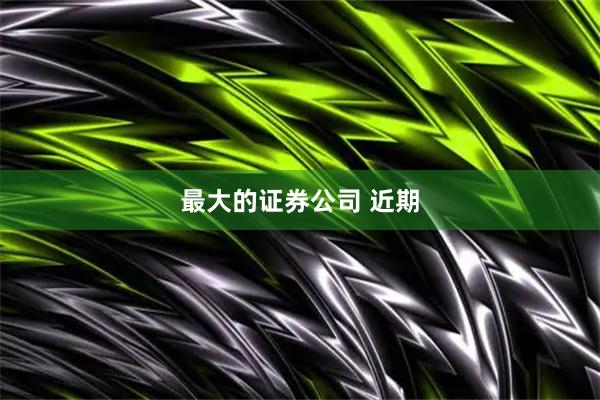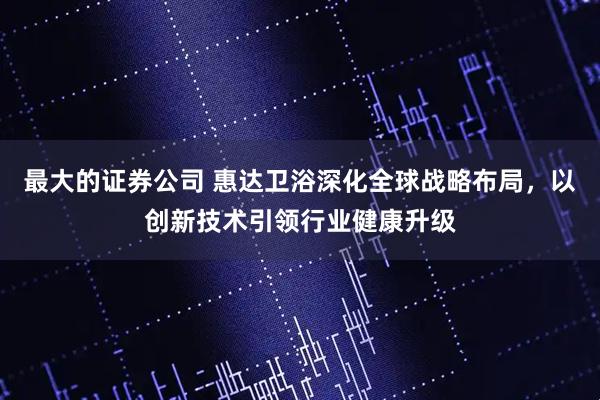整个港城都知道最大的证券公司,我和陆振川的命是拴在一起的。
当年大暴动,他脊骨中刀,我小腹被钢筋贯穿,我俩从死人堆里爬出来,才有了后来的和联胜。
三十年,我们无一子嗣,他是我唯一的亲人。
他跟我说,老天不给我们孩子,是怕我们把命分给旁人。
我信了。
直到我五十岁生日,亲手推开那间他为我供了三十年长明灯的禅房。
檀香混着苟合的味道,一个能当我女儿的女孩,从他怀里抬起头。
和她对视的瞬间,我好像看到了另一个自己。
一个年轻的,干净的,纯真的自己。
陆振川替她拢好衣服,看着我,眼神没有半分愧疚,只有岁月磨平一切的漠然。
“阿兰,你老了,火气不要这么大。”
我笑了,缓缓拔出腰后的枪,顶在他的额头。
“是不大,所以今天,我只杀一个。”
展开剩余88%在我扣下扳机的瞬间,陆振川的反应快如闪电。
他猛地将怀里的女孩扑倒在地,子弹擦着他的耳廓飞过,狠狠嵌入了后面的梨花木佛龛,木屑飞溅。
禅房里死一样地寂静。
陆振川趴在地上,用身体死死护住身下的阿月。
他缓缓抬起头,那张永远波澜不惊的脸上,第一次出现了真正的震怒和不敢置信。
“徐慧兰,你来真的?!”
“不然呢?”
陆振川皱了皱眉,侧过头,对怀里那个吓得瑟瑟发抖的女孩说:
“阿月,别怕,自己先把衣服穿好。”
女孩的脸苍白如纸,哆哆嗦嗦地抓着凌乱的衣衫。
一双眼睛惊恐地望着我,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
这副我见犹怜的模样,确实是我二十岁时最擅长的伪装。
陆振川这才把视线转回我身上,语气像是训斥一个不懂事的下属。
“徐慧兰,把枪放下。今天是你的生日,别闹得太难看。”
“难看?”
我重复着这两个字,嘴角的笑意更冷。
“陆振川,三十年前,你背着肠子快流出来的我,走了十里血路,那才叫难看。今天这点事,算什么?”
我的话让他眼中闪过一丝复杂,但稍纵即逝。
他看着我,竟然叹了口气。
“阿兰,你看她的眼睛,多像你当年。天不怕地不怕,就那么看着我,我就是为了这双眼睛,才愿意把命都给她。”
他说的是“她”,不是“你”。
我懂了。
他不是在怀念我,他是在怀念那个能让他拼命的自己。
而现在,我老了,不值得了。
我扣着扳机的手指,稳得没有一丝颤抖。
跟在我身后的心腹阿彪,已经默默带人堵住了禅房所有的出口。
今天这里,一只鸟都飞不出去。
陆振川终于意识到我不是在开玩笑,他的脸色沉了下来。
“你非要这样?”
我没回答他。
视线越过他的肩膀,落在那盏供在佛前的琉璃长明灯上。
灯芯里的火苗,已经安安静静地为我燃烧了三十年,见证了我们从一无所有到执掌和联胜。
真刺眼啊。
下一秒,我手腕一转,枪口偏移。
“砰!”
一声巨响,再次撕裂了禅房的宁静。
子弹没有射向他,也没有射向那个女孩。
它精准地击碎了那盏琉璃灯。
灯座四分五裂,火光瞬间熄灭,一缕青烟袅袅升起,带着最后一点温度,散在冰冷的空气里。
禅房,暗了。
女孩的尖叫声终于冲破喉咙,而陆振川的身体,在那一刻僵住了。
他难以置信地看着一地碎片,脸上的血色褪得干干净净。
他不怕我杀他,却怕我亲手毁了我们的过去。
我走到他面前,用还带着硝烟余温的枪管,一下一下,轻轻拍着他僵硬的脸颊。
“陆振川,我们这种出来混的,没有离婚,只有丧偶。”
我盯着他的眼睛,一字一句:
“这句话,三十年前,你教我的。”
他的瞳孔猛地一缩。
我俯身凑到他耳边,落下最后通牒:
“现在,我给你机会选。”
“要么,签了离婚协议,滚出和联胜,我当这个世界上再没你这个人。”
“要么…”
我直起身,枪口重新对准他的眉心,眼神里再无半分温度。
“我亲自送你去投胎,下辈子,做个干净人。”
我回到家时,天已经擦黑。
别墅里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,所有下人都屏着呼吸,连走路都踮着脚尖,生怕惹上我半分煞气。
我脱下染上檀香和硝烟味的外套,随手扔给管家,径直走进我的茶室,为自己泡了一壶滚烫的普洱。
茶香袅袅,驱散了禅房里那股令人作呕的味道。
我没等太久,陆振川就回来了。
他换了一身衣服,脸上看不出半点在禅房里的狼狈,又恢复了和联胜龙头该有的沉稳。
他挥手让所有下人退下,偌大的客厅只剩下我们两人。
他拉开我对面的椅子坐下,亲自为我续上一杯茶。
“阿兰,我们三十年夫妻,你至于为这点小事动枪吗?”
我端起茶杯,吹了吹浮沫,眼皮都没抬。
“小事?”
我轻笑一声,“你在我的佛堂里,碰一个能当你女儿的人,这也是小事?”
他被我噎了一下,脸上闪过一丝不耐,但还是压着火气解释。
“她只是个孩子,长得有几分像你,我一时糊涂。”
他把这番话说得轻描淡写。
“你跟我风风雨雨三十年,什么人没见过,何必跟一个不懂事的小丫头计较。”
这话说得真好听。
把背叛说成怀旧,把苟合说成糊涂,再把我的愤怒,定义成跟小丫头计较。
见我不说话,他以为自己的话起了作用,身体前倾,试图来拉我的手。
“阿兰,我知道你五十岁生日,心里不痛快。女人到了这个年纪,是容易胡思乱想,火气也大。”
他的手指即将碰到我的手背时,我反手将滚烫的茶水,尽数泼在了他伸过来的手上。
“嘶——”
陆振川猛地缩回手,手背瞬间红了一大片。
他难以置信地看着我,眼神里终于有了压不住的怒火。
“徐慧兰,你疯了!”
“我疯了?”
我缓缓站起身,居高临下地看着他。
“陆振川,我看是你老糊涂了,忘了这家,忘了和联胜,是谁陪你一刀一枪打下来的。”
我俯下身,凑近他的脸。
“你觉得我老了,不中用了,没法给你生儿子了,所以找个年轻的子宫,延续你陆家的香火。说得这么冠冕堂皇做什么?”
他瞳孔一震,没想到我把话说得这么直白,一时竟无言以对。
我直起身,拿起手机,当着他的面拨通了阿彪的电话。
电话很快接通。
“大嫂。”
“阿彪,西环码头今晚是不是有批海鲜要上岸?”
“是,大嫂,川爷的货。”
我瞥了一眼脸色铁青的陆振川,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笑意。
“最近风声紧,让水警兄弟们辛苦辛苦,过去查一查。”
“收到。”
我挂断电话,将手机扔在桌上。
陆振川猛地站起来,一把攥住我的手腕。
三十年前在暴动中为他挡刀留下的旧伤,就在他此刻紧攥的地方,一阵阵地刺痛。
“你敢动我的货!”
他双目赤红,咬牙切齿地低吼。
我抬起头,迎上他愤怒的目光,眼神里没有半分畏惧,只有一片荒芜的冷意。
“陆振川,这只是个开始。”
“你让我不痛快,我就让你不痛快。你让我活不下去,我就让你——”
“死无葬身之地。”
【 查看后序内容 请点击】最大的证券公司
发布于:江西省豪瑞优配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